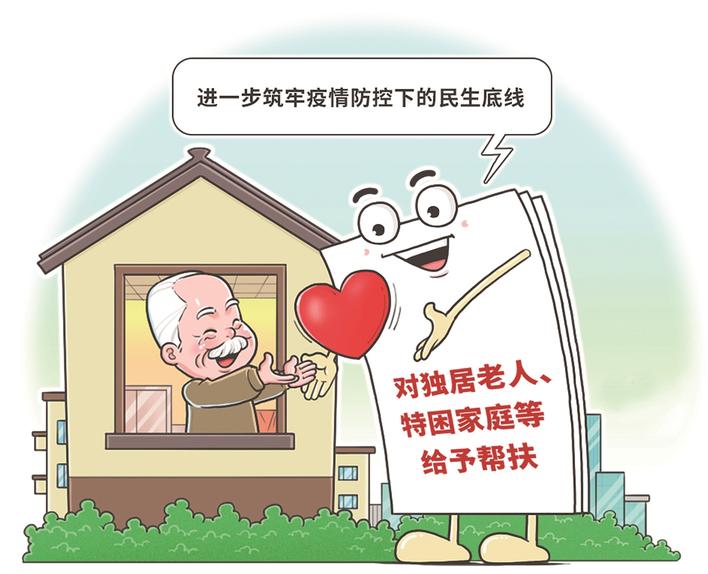□伏秀平 吴洪锋 王静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基层单元,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搞好社区治理对于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意义重大。
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社区的精细化治理和网格化治理是技术层面的手段,而在主观层面还应进一步增进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提升其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这对于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根基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镇化进程深化推进,人口流动性加剧,基于居住地选择的社区邻里关系逐步取代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熟人社会,陌生人社区已经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形态,传统意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形成基础正在逐步瓦解。因此在当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重建亟需以社区为载体,重塑自古以来的邻里守望、互助互爱的基层社会秩序力量,其中的核心要素就是在社区群众的主观认知层面,通过社区文化引领加强社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共同推动社区发展,维护社区治理的成果和成效。就现实路径来看,如何加强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需要从以下角度给予重视和政策倾斜。
着力强化民生服务发展。文化心态是建立在基础民生需求之上的意识形态,只有先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关注群众多样化的现实需求,精准有效化解难题问题,顺应民意期望,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惠民、利民的举措,才能真正激发出公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肯定,才能真正增强公众对于城市发展的信心和热爱。这其中包括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养老服务、基础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服务、休闲娱乐需求、治安保障、生态环境、社区公共设施等关乎群众生活质量的设施建设与服务提供。
畅通居民表达诉求和参与议事的平台和渠道。根据各类型社区特点,积极打造方便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形式多样的社区参与平台,完善居民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当家做主的权利行使机制,既有利于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也保证了所制定政策的民主性及科学性。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居民诉求回应机制,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夯实责任,问题前置,主动治理,快速有效回应居民诉求,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只有这样通过共同努力建成的家园,群众才会倍加珍惜,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育也会水到渠成。
开展志愿服务。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慈善服务力量,能够高度彰显出社会文明程度和社会关怀程度,能够有效弥合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裂痕和社会服务的不足,以志愿者的爱心和责任心激发社会之中守望相助和互帮互爱的力量,改变冷漠、道德滑坡、信任缺失等现代社会的不良文明风向。因此必须加大力度发展社会志愿服务队伍,给予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社区服务建设、开展专业化群众服务、发展慈善事业、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渠道,以此来逐步提升民众的公共意识和文化认同感。
强化本土化认知。城市文明的维护和文化的延续必须依靠群众,而不单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和工作,比如大运河文化集中体现了历史延续和生态文明的结合,是地域文化的符号,运河文化如何进一步凝聚群众热爱运河、保护运河、宣传运河的意识,是文化心态在器物层面的重要体现,并以此强化公众对于地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是社区文化认同感培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本土化的文化感召力,以加强群众对于维护社区家园和城市发展的驱动力。
文化教育持续深入。先进文化的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点内容,但当下还应认识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必须深度衔接,才能够从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认同感,带动自身家庭去贴近社会发展的秩序需求。此外,社区应是影响人的成长的重要社会化环境,因此社区教育应进一步融入学校教育之中,通过社区来提升学生的责任意识、关爱意识、问题意识和解决能力,就体现得更为直观有效。
建立以党建为核心、以法治为保障的奖惩机制。公共素养的层次决定了任何一项建设必须配备有效的奖惩机制,一方面激励激发公众维护文化环境、创新文化元素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惩戒破坏文化环境的负面行为。但激励和惩罚不是毫无标准的,因此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是要在党的核心领导下,充分建立起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让奖惩办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强化责任,规范执行,严格监督,形成文明奖惩的长效机制,推动公众文化行为和思想逐步走上良性轨道。
社区治理任重而道远,同时也必将是一个系统化工程,需要在群众主观认知层面、物质保障方面、政策导向方面协同发展,方能取得切实的效果和社会效益,切实提升群众生活的满意感和幸福感。
(作者单位:沧州师范学院政史系)